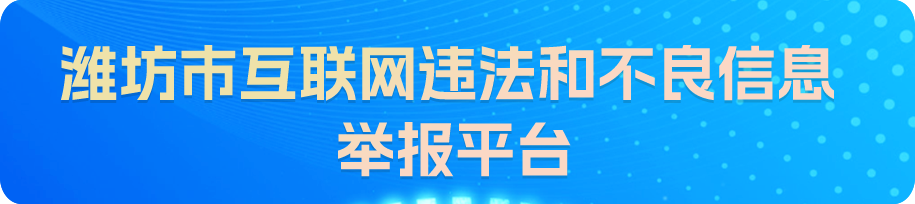老家的滋味 (一)
◎王庆德
老家在青州玲珑山北麓。因处城西南,被称作西南山里。这个称谓准确又含有封闭的意味。无妨,我只念着它的好。
这里青山、绿树、碧水、沃土,无一不佳。春花、秋月、夏云、冬雪,无一不美。红的樱桃,黄的杏子,硕大的苹果,独具特色的蜜桃,果子三季不断。过了寒露,山楂簇簇,如朱砂点染枝头;柿子累累,如繁星散落,红遍了山岭沟坡。这些景物让人流连,饱人眼福。而更让我魂牵梦绕、记忆清晰、不时回味的其实是吃。这是口福,比看深刻得多。试说几品,与诸位共享。
捻捻转
你吃过吗?大概连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吧。
这是一种用新鲜麦粒制成的吃物。
在小麦秸秆尚绿,而籽粒已经饱满的当儿,割上一捆,扛回家来。母亲生火,婶子一把一把地抓着麦穗在火上燎。麦穗的香气,刹时满了天井,飘出了街巷。
燎过的麦穗,麦粒一搓即脱。筛去麦糠,麦粒儿滚圆,黄中泛绿。不只香气诱人,那色泽也吸引人的眼球,真想抓一把放进嘴里。可再馋也不让吃,还有一道工序。
将一簸箕麦粒端到石磨上,均匀地撒进磨眼里。磨盘转动,筷子般的细条旋转着,从磨缝里吐了出来。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……挂在磨的下端,这就是“捻捻转”。
磨盘不断转,捻捻转渐转渐长。我忍不住拽下几条,跑出磨坊,塞进嘴里,黏黏糯糯的香,微微的甜,嚼来嚼去,不忍下咽。
将捻捻转收在瓦盆里。太阳下山,父亲、二叔从坡里回来,每人抓一把,尝尝鲜,剩下的母亲端进了堂屋。我知道,这是留给我解馋的。
一个花甲过去,各种食品花样翻新,让人眼花缭乱,却没有哪一种可以比拟捻捻转。如今,母亲归去,磨子没了,捻捻转也见不到了。
雪里趴
刚进腊月,飘了一场小雪,我拽了一床棉被,倚在床上读诗。门“吱呀”一声,堂弟走了进来,笑着说道:“天冷,送你点下酒菜。”一边说着,一边递给我一个纸包。打开一看,是一堆干蚂蚱。
我对蚂蚱并不稀罕。小时候,上坡割草,常常是先扑上一串蚂蚱,找一些干草,把蚂蚱烧熟吃光,这才开镰。看这包蚂蚱也没什么特别,顺手放在了条几上。
夜有三更,窸窸窣窣声把我惊醒。声自纸包而出。急忙打开,蚂蚱正伸腿跧爪——全活了。
第二天,我问堂弟,看上去已经干了的蚂蚱,怎么又活了?
堂弟笑道:这蚂蚱叫“雪里趴”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动了,便趴在前坡的玉米秸里避寒。时间一长,肚子里的东西消耗干净,趴以待毙。这个时候,掀开玉米秸,蚂蚱一动不动,只管下手捡就是了。
妙哉!
从小在山里长大,只知道扑蚂蚱、烧蚂蚱,还未曾尝到这通体无污秽的“雪里趴”呢!
次日中午,堂弟下厨,花生油炸“雪里趴”。瞬间大盘端上。看“雪里趴”那头、那翅、那腿、那爪,还有那细长的躯干,通体焦黄。夹一只放入口中,毫无顾忌地咀嚼。那酥、那香,只可体味,难以言传。
我想,齐白石老先生画虫是一绝,连昆虫学家都叹为观止。让他老人家看看,尝尝,爰笔图之,传之于世,让世人皆知“雪里趴”,那真是一件幸事。
烧柿
先解释一下题目。烧柿的烧字,这里不作动词,是说柿子的一种吃法。
柿子有多种吃法。将柿子放于筐中,置日光下晾晒,待以时日,由黄变红,由硬变软,涩味褪去,即可食之,此之谓烘柿。
把柿子用桃核啄了,铺上桑叶,用温水泡上两天,柿子遍体布满浅黑花纹,咬一口挺脆,此之谓漤柿。
将柿子去皮、晾晒、倒籽、团饼,然后避光置放数日,使之渐干而生霜,此之谓柿饼。
这些吃法,众人皆知,这里我只说烧柿。
所谓烧柿,就是将柿子用火烧了吃。霜降一过,柿子红了。挑个大、色深、平顶的柿子,摘上一篮。垒起尺半高的两段短墙,墙上横置十来根木棍,将柿子平排其上,在底下生起火来。柴要干,火要旺。噼噼啪啪,烟火升腾,把柿子底面烧焦。熄火,翻转,再烧。烈焰闪烁中,柿子通体变为焦黑。挑下木棍,用余火再焙。半小时许,柿子熟了。
将柿子从火灰中扒出,雪白的柿乳从焦黑的柿皮中溢出,散发着特有的香甜气。捏着柿蒂,放进清泉水中一拔,那焦黑的皮一撸全脱。仿佛川剧变脸,焦黑的柿子立时变成了紫红,像一颗大大的紫水晶。
这样的柿子一定要趁热吃。一凉,味道就寡淡了。因为太热,吃时“吸溜儿”声不断,三五口一个烧柿便下肚了。我一次能吃五六个。一位堂兄能吃一扁担——将烧柿一个个排起,排到扁担那样长,他从这头一气吃到那头。问到底吃了多少个,忘了,只记得一扁担,“一扁担”就成了他的绰号。
韭花
我说的韭花,不是园子里韭菜开的花,是山韭花做的酱菜。
老宅三面环山,山山有韭,野生。较园中韭,叶瘦而硬,入口不爽。它的花倒是好东西,香气浓,辣味重。
夏历八月,山韭蹿薹,一朵朵白花绽在薹上。这个季节,山坡还是绿的,朵朵白花在风中摇曳,稀稀落落地散在山坡上,老远就看得分明。几步一朵,不到半天就采一筐。
将采来的韭花洗净,撒上一把盐,上石磨细磨。磨盘呼噜呼噜地转,韭花糊徐徐地下。那浓郁的韭花香充满了磨棚,沁着人的心脾。这样韭花糊即能趁鲜吃。可鲜则鲜矣,味非至佳。将韭花糊置入瓷坛,封严,发两个月,方臻至味。
韭花与豆腐最搭。用卤水点一锅热豆腐,启开瓷坛,盛出韭花,滴上几滴香油,这便是一道素菜——韭花蘸豆腐。雪白的豆腐散着淡淡的清香,墨绿的韭花溢着浓郁的韭香。大快朵颐,既作菜,又当饭,可口、养胃。此可谓庄户人家的名吃佳肴。
韭花不只是庄户人的菜,达官贵人也爱吃。唐末五代时的杨凝式官至太子太保,书法承唐启宋,颇具影响。他在《韭花帖》中说:“当一叶报秋之初,乃韭花逞味之始,助其肥羜,实谓珍羞(馐)。”肥羜者,羔羊也。以韭花佐羊肉,我也曾吃过,可如今羊肉有胡椒为佐,抑了韭花的鲜,总感到不及韭花蘸豆腐来得清纯。
编辑:孙锦
一审:孙锦 二审:冯媛媛 三审:李中伟